
一、主持人:IB高二2班王映懿

鲁迅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从小学到高中的课本里,都有他的作品,但在我们的意识中,他似乎是一个早已属于过去的人,与我们的生活有着不小的距离。在我们的校园里有一座鲁迅纪念馆,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南京鲁迅纪念馆的新展也在此时开幕。这座纪念馆有着怎样的历史,鲁迅与我们又有怎样的联系呢?有请展览的策划者IB郑敏虹老师。
二、发言人:IB教师郑敏虹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谈谈鲁迅纪念馆的展览,我想很多同学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校园里会有一个鲁迅纪念馆,鲁迅在这里读过书吗?他是附中校友吗?这件事情要从123年前说起。123年前,也就是1898年,一个叫周树人的年轻人离开家乡绍兴,来到南京求学,他先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不大满意,半年后转考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在这里学习三年后毕业。江南陆师学堂位于城北,在今天的中山北路与察哈尔路一带,学堂里的建筑基本是平房,今天已不存在,但有两栋砖木结构的小楼保留至今,一栋是总办办公楼,位于现在的鲁迅园社区,另一栋是德籍教员宿舍楼。听到这里,大家或许猜到了,这正是校园里的南京鲁迅纪念馆。1957年,这栋楼被列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南京鲁迅纪念馆成立并对外开放。迄今为止,全国一共有六家鲁迅博物馆/纪念馆,分别在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六个鲁迅生活过的城市,南京是唯一建在中学校园内的。2018年,我们有感于十多年来鲁迅研究的新成果与博物馆展陈方式的更新,在原有陈列基础上启动了新的展览计划,历经两年的内容编写、一年的陈列设计和半年的施工布展,于今年9月正式完成,进入试运行阶段。新展新增了两百余件展品,以“寻求别样的人们”为题,以“鲁迅”、“新学”、“青年”为关键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纪念馆的一楼,历时性地展示青年鲁迅与南京的三次相遇,第一次是以“周树人”的名字在南京生活学习的学生时代,这一时期正逢晚清洋务运动中“新式学堂”的开创和新思想新文化的流行,它是鲁迅接触现代科学、阅读翻译文学、探索精神启蒙的重要人生起点,也是他最高兴回忆的青春时光;第二次是在鲁迅赴日留学归国后,他先后在浙江杭州、绍兴的中学讲授自然科学,1910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鲁迅率领200多名绍兴师生前来参观,开拓眼界;第三次是在1912年,民国肇造,鲁迅赴临时教育部任职,再度来到南京。可以说,青年鲁迅的经历中包含了近代教育的变革与一座城市的记忆,南京也见证了这位思想者孕育的过程。展览的第二部分在纪念馆的二楼,聚焦于受到鲁迅影响的三个青年人:胡风、巴金和黄源。南京师大附中前身为以“新精神在全国驰名的”东南大学附中。1920年代,三位受“五四”感召的年轻人曾在此就读,并与鲁迅相识于30年代的上海,共同投身文艺批评、编辑出版与文学翻译事业。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纪念先生最好的方式是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我们希望这两代“新青年”的经历能带给大家启发,去勇敢地尝试,认真地付出,寻求自己“别样的”人生。
三、发言人:IB高三2班陶语奇、袁加琪

陶语奇:哎,袁加琪,开学初的鲁迅纪念馆参观你去了吗?
袁加琪:去了,很荣幸作为第一批观众参观,也很幸运自己就读的学校与鲁迅先生当年学习的地方如此之近,让我有机会跨越时间,在空间上近距离接触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陶语奇:是啊,想到参观的是鲁迅纪念馆,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庄重起来。你还记得刚走进去的感觉吗?
袁加琪:嗯……我的感觉是:别有洞天。一个个小房间按照历史时间顺序依次串通,错落有致。我们的思绪跟随着少年鲁迅的行动轨迹,从南京到了东京,再回到中国的杭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段内容是江南水师学堂发生的学生械斗,以及鲁迅对学校的吐槽和“反抗”。即使如鲁迅这般人物,少年时也和我们多数学生一样,好鲜活啊!
陶语奇:哈哈,是的,你还记得鲁迅自刻的那方“戎马书生”印章吗?简直是这份火热的少年心留下的最有趣的证据之一。我想起《呐喊》自序的开头,鲁迅说自己“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在陆师学堂的学习经历应该就是这些梦的素材来源吧。学堂里开明的风气鼓励学生阅读新书和翻译作品,正是在这里,鲁迅接触到进化论和外国文学,使他的思想大受震撼。我看着这枚虎头虎脑的印,一股青涩蓬勃的少年气息瞬间扑面而来,仿佛在学堂就读时的鲁迅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的某个同龄好友一般——总是自命不凡、卓尔不群的模样,一有空就往图书馆里钻;你要去向他询问或者请教,他又会立马真挚热忱地滔滔不绝……看着这样的鲁迅,我和好几位同学不禁相视而笑。
袁加琪:喔,有画面感了。其实,我本身不算是很有耐心的人,阅读文字,尤其是毫无故事性的文字时,很容易分心走神开始发呆。但纪念馆里每一处文字的旁边,总会配有相应的文物或照片,让我保留住好奇心和兴趣,持续把注意力放在内容上。除了拥有展馆基本的展板、展柜、展品外,这里还设置了互动查询屏、听筒、可翻阅的书籍、雷达互动投影等多个互动设施,让观众在了解鲁迅经历的同时还能够沉浸式地体验,感受那个时代的环境和氛围。并且我注意到,这些“高科技”并没有打破馆内的书卷气,而是通过室内设计很好地融合了进去。
陶语奇:是啊,展馆中的一些小设计非常贴心:墙上听筒里咿咿呀呀的绍兴话、可供翻阅的活页资料、一接触就有介绍框弹出的雷达互动地图……这让参观过程妙趣横生。玩着鲁迅带领绍兴师生来南京参观的南洋劝业会地图,我好像也跟随着他们进行了一次社会实践field trip呢。
袁加琪: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喜欢,就是二楼的阅览室。林立的书架旁摆放着长书桌,我扫了一眼书架,看到许多研究鲁迅或是鲁迅作品的书籍,还有很多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它们让我感觉到我们在展厅的了解和学习似乎并没有止于那里,而是延伸了更远,让想要继续深入了解鲁迅的人们尽情翻阅相关的书籍文献,把一切想了解的东西给读个畅快,这个空间的存在让我很惊喜。
四、发言人:IB高二2班陈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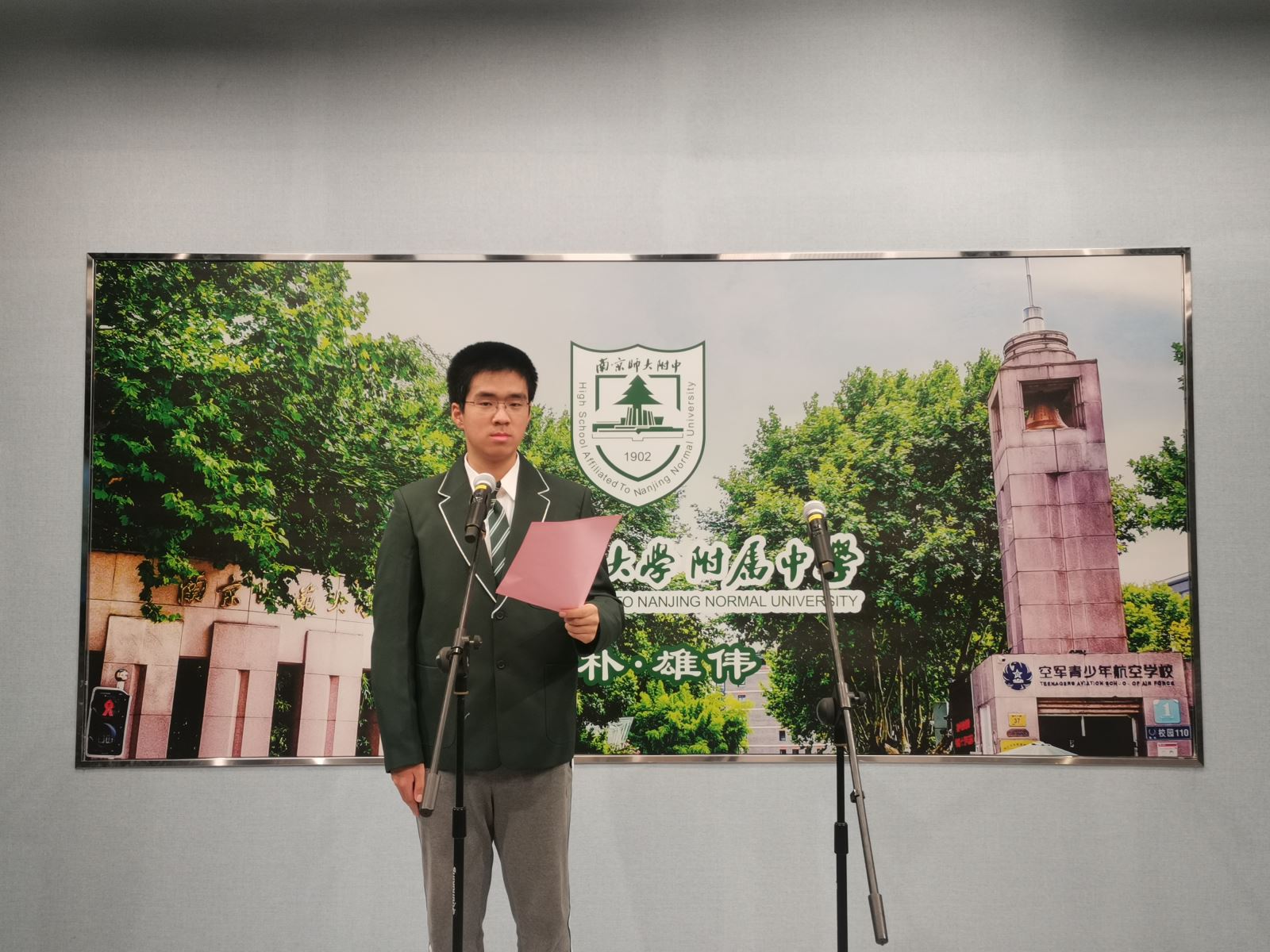
这学期,我加入了鲁迅纪念馆志愿服务社,这是一个全新的社团。在此之前,我对鲁迅知之甚少,希望借此机会能够走近鲁迅先生。在社团中,我担任了导览志愿者一职,负责导览的展厅主要呈现的是鲁迅与青年作家的友情。鲁迅一生爱护过的青年人很多,有三位和我们附中息息相关,他们是胡风、巴金和黄源。这三位学长都曾经在东大附中读书,当时的东大附中以其新精神驰名全国,托尔斯泰的《复活》、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与鲁迅的《呐喊》都是年轻人爱读的书籍。在展厅里,有一份珍贵的文献,《东南大学附中周刊》。这份出版于近90年前的校刊是由当时的学生自主创办的,他们在周刊上讨论学校改革、关注社会发展,为不同的观点辩论,青年胡风曾担任过《周刊》的总编辑,而正读高三的巴金则是这份校刊的热心读者。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东南大学附中周刊》出版特号声援,胡风也投入进了社会运动。但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巴金的小说《死去的太阳》记叙了学生们从热情高涨到希望幻灭的过程,胡风在自己的诗里也写道:“我从田间来,/抱着热血满腔——/叫我洒向何处呢,/对着这无际的苍茫?”理想与现实碰壁后的迷茫是年轻人常有的,作为过来人的鲁迅先生对此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倒较为切实可靠罢”。“做自己本份的事”,这是鲁迅对胡风所说的话。于是我们看到,他们一起合作写评论,推出文学新人。萧军和萧红从东北流亡到上海时,生活无着,籍籍无名,萧红的第一部小说是鲁迅先生亲自动手,认真修改全书,并撰写序言;胡风则为小说确定了“生死场”的书名,写了后记。在合作完成《生死场》的过程中,鲁迅慷慨帮助默默无名且结识不久的晚辈作家,以实际行动呵护、提携青年,对胡风有很大的影响,在鲁迅逝世后,他延续了鲁迅的精神。鲁迅与巴金的关系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的“倾向很不同”,直接交往也不算多,但鲁迅一直信任巴金,支持他的出版事业,因为,“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从他们往来的书信上,我们能看到“认真”的鲁迅让巴金感受到的温暖。还有《译文》杂志,这是由鲁迅、茅盾与黄源共同努力创办的。创刊时,鲁迅花费了很大心血,尽管第四期后由黄源负责编辑,鲁迅仍尽己所能,不辞劳苦地帮他找译稿和插图。在黄源遭遇出版社不公正待遇时,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他说话。看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如此爱戴鲁迅,怀念鲁迅了。展厅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希望我的导览能让大家感受到鲁迅与青年的珍贵情谊与他持之以恒的人格魅力,也希望我们的社团能像前辈的事业一样,长久地、认真地做下去。